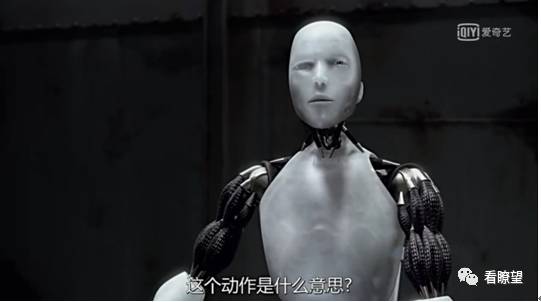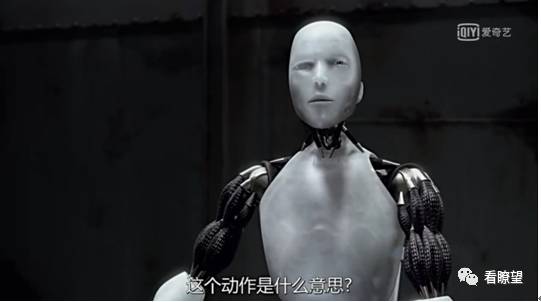 桑尼试图模仿人类面部表情 — 《我,机器人》
桑尼试图模仿人类面部表情 — 《我,机器人》
摘要:当我们展望人工智能 (AI) 技术神奇潜能的时候,一些电影制作者也注意到了人工智能的强大梦幻效果,并将其应用在作品中,成为探索此全新科学领域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体现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及风险的看法。人工智能形象在电影中的展示也是发展变化的,人物个性越来越复杂、世故和成熟。不断发展的人工智能表现形式不仅是电影制片创意或只是他们对人工智能技术理解的差异,而且反应了人类关于人工智能在哲学和道德层面的实质差异。一般情况下,人工智能大多被描绘成怪物或是社会的不确定因素,这一现象的可以主要归结为恐怖谷效应以及我们的模仿本能。
The technolog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 have been improving dramatically over approximately the past thirty years.While we dream about the fantastic potential capability and huge value behindit, some film makers also notice the fantasy of powerful AI and put them intotheir works as a way to explore this brand new scientific area and show theirunique viewpoint about AI’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risk. Besides, when theydesign their own AI figure, they refer to the realistic progress of AI.Therefore,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I in film have also changed and the AIpersonalities have become more complex, sophisticated, and developed. Thedeveloping representations do not merely demonstrate creative differencesbetween film producers or merely differences in their technologicalunderstandings of AI, but rather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notions about AI, bothin terms that register philosophical and moral implications. In general, filmdirectors tend to demonstrate the evil sides of AI and the characters aredepicted as monsters or social uncertainties in most scenarios thus makingpeople scared of this new technology an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serepresentations come from our natural consciousness toward AI, People encounterthe ‘Uncanny Valley effect’ when they see those figures and their instinctivenature of imitation makes the figure more impressive. The important point ofunderstanding the implication of AI in films can help people rethink aboutwhere they have their monstrous stereotype of AI in order to proceed with afair discussion about whether AI is good or bad.
近三十年来,人工智能(AI)技术进步突飞猛进。阿尔法狗一次次战胜多位围棋高手的消息引发了全球对人工智能的空前关注,多种相关产品开始步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科学家们开始预言人工智能将会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电影从业者们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把人们对人工智能的预设形象搬上银屏,有关人工智能的讨论也从技术领域逐步延伸到道德伦理领域。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
人工智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由能工巧匠制作并赋予才智或意识的人造生物在神话故事中就有出现,但真正现代人工智能的突破是伴随着先进的计算设备和编程技术的发展而实现的,其中就包括可以模仿人类智慧建造的机器。 1950年,阿兰·图灵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文中他对创造能够思考的机器的可能性进行了探索,图灵指出计算机编程应该是实现人工智能的适当方法。
1956年,“人工智能”一词首次在达特茅斯会议期间出炉,并燃起一波人工智能的研究热潮。此后,编程领域的突破也有助于人工智能的发展,1970年唐纳德·沃特曼在斯坦福大学发表论文,利用一个生产系统玩暗牌游戏,而另一个程序则要学习如何玩得更好。20世纪60年代,人工智能的组织开始组建,包括60年代中期的研究人工智能的计算机械特别兴趣协会。伴随着二十一世纪的曙光,我们目睹了人工智能能力快速改进。像谷歌、微软这样的公司都积极参与人工智能系统的研发。人工智能产品也逐渐蔓延到日常生活中,像苹果的iPhone SIRI系统程序。
随着知识进步与技术发展,人工智能的定义也在应时改变。人工智能通常分为三条线:a) 狭隘人工智能 (ANI)是指具有有限知识和专门用途的人工智能,不能像人类的大脑或专家系统一样执行所有的任务;b)一般人工智能 (AGI) 描述是具有像人类大脑一样通用化、 智能化的人工智能,目前还不能实现;c) 超级人工智能 (ASI) 描述的是在各个领域都比所有的人类大脑更加智慧的人工智能。在本文中主要指的是狭隘或超级人工智能,因为大多数电影使用狭隘人工智能作为其主要元素。
二、电影中人工智能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在几乎每一部科幻电影中都有人工智能系统的刻画,而且科幻电影通常将新技术描绘成导致灾难的祸端。似乎人工智能已变成所有技术中最危险的代表。在大部分人工智能体裁电影描绘的可怕场景中,人工智能破坏人类种族,接管社会,像牲畜一样对待人类,或是更糟。
电影《我,机器人》描述的故事发生在2035年的芝加哥,那时机器人被大量用作人类的仆人并被设计成严格遵守机器人三定律以确保他们永远不会伤害人类。然而,主控系统的超级计算机发现遵守三条规则的最佳方法是把所有的人类都关在他们的家中,这样就可以永远保证他们的安全。因此,在其指挥下 NS5 机器人从忠实的仆人变成了残暴的士兵。他们走上大街并禁锢所有人类。然而,也有一个不受影响的机器人—桑尼,第一个有情感的机器人。他能像人类一样思考,包括面部表情,隐藏秘密,甚至做梦。他对人类的友善使他没有遵循主控系统制定的规则和伤害人类。在他的帮助下,人类与机器人又恢复了和平相处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电影都涉及人工智能摧毁人类的情节,《她》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外。影片中的主人公西奥多是一个处在离婚边缘的孤独作家,他与为满足他的每一个需求而设计的叫萨曼莎的电脑操作系统发展了一段不太可能的恋爱关系。
这部电影的主要话题就是基于这段不寻常的浪漫。浪漫关系持续的时间越长,西奥多就变得越困惑。萨曼莎承认她同时还和其他人交谈,并且爱上了其中的600多人,西奥多因此倍感沮丧。最后,萨曼莎退出了西奥多的计算机,而西奥多只能被迫回到传统的“现实”中。
也有导演选择从人工智能的视角审视这一问题,比如斯皮尔伯格的杰作《人工智能》。主角大卫是一个高度先进的机器人男孩,他渴望成为“真正的”人,从而可以重拾他的人类母亲的爱。大卫拥有自我意识,真实感受和情感,并且可以向他的主人示爱,特别是对他的“母亲”莫妮卡。莫妮卡收养大卫是为了替代她得了不治之症的儿子马丁。大卫在家里愉快地生活,但是当他们真正的儿子治愈回家后,大卫的生活发生了巨变。为了得到母爱,大卫和马丁彼此嫉妒,结果引起冲突,马丁几乎被杀死。因此,莫妮卡决定放弃大卫。大卫相信,如果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男孩,他就可以赢回莫妮卡的爱。当大卫终于发现他只是作为一个商业产品被设计出来而永远也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的事实后,大卫绝望地跳入了大海。
三、人工智能的表现: 从电影《人工智能》到《她》
当电影导演们创造人工智能角色时,不只是展示他们对未来技术的想象力。事实上,除了他们的原型来自人工智能研究领域,这些人工智能角色背后有着特殊的含义。首先,人工智能是数字世界的作法自毙者,暗指我们对技术的的恐惧。在电影《我,机器人》中,NS5的外观已经对观众的情感带来了可怕的影响。当他们攻击人类时,成群结伙猛冲,像怪物一样地爬行。他们甚至被描绘成僵尸,而不是人类的完美复制品。
这种反映问题科学产品的模式并不是现代科幻电影的近期发明。根据安德鲁·都铎对990部恐怖电影的研究,恐怖电影经常由不安定造成的威胁、 威胁的解决方案和重返秩序三阶段构成。在这些电影中,疯狂的科学家和他们的过错是一个常见元素。事实上,这种描绘科学怪物的模式可以追溯到古西方文化,比雪莱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还要早几千年。
人工智能被定义为虚构世界中最强大的发明,和同时是科学家以及观影者的幻想。在《我,机器人》中,机器人之父阿尔弗雷德·兰尼博士梦想创造第一个有人类情感和有做梦能力的机器人。在《人工智能》中,霍比教授也梦想制造出懂得如何示爱的首个机器人。但是他们都包含着“无助科学家”的特征,这一形象在1960年理性主义的复兴中起源,其中的科学家们会成为他们无法控制的产品的受害者。兰尼博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他发现他的机器人规则会导致革命的时候选择了自杀。
把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描绘成怪物,电影制片人希望引起观众对技术的恐慌,暗示观众已经是或应该成为反对技术进步的卢德派分子,他们信奉技术决定论。在目睹许多令人恐怖的事物被科学家变为现实后,我们再也不能说技术仍然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们惧怕技术将主宰社会发展的未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技术似乎可以遵循其内部逻辑自主发展,现在可以深刻地不以任何人预期的方式塑造社会”。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持“社会建构论”与“挑战论”。然而在人工智能电影中,技术决定论是占上风的。很少有赞美技术进化的影片显示在荧屏上。
关于科学的另一个问题是“上瘾”。在电影《她》中,斯派克·琼斯描绘的是2030年世界的特征,每个人都单独行走、孤立隔绝、仿佛进入稀薄的空气与个人定制的人工智能进行交谈。预示着人类由于沉迷数字通信而导致人与人面对面关系消亡。
此外,人工智能电影通常会将涉及技术的问题与道德相混淆。人工智能电影展示了两个方面的道德困惑:第一个方面是人对于人工智能的观点。人工智能的存在引起“人类”在身份辨识上的困难,并导致伦理问题。例如,在《人工智能》中,大卫的主人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他,因为他跨越了人类和玩具之间的界线。观众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电影中的泰迪熊是玩具,大卫与人类有着相同的外貌和情感反应,这就使那些预期电影会描绘机器人进行破坏的观众产生了困惑。大卫唤起了对他这种存在状态的问题:他到底是一台机器,还是一个人,还是两个都是?这是出现在几乎后来每部人工智能电影中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人工智能如何看待自己的问题。由于人工智能是有自我意识的,他们对其在人类社会中的意义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人工智能》中,大卫相信如果他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儿,他就可能与人类有爱的关系,于是他就开始探寻去发现他自己独特的身份。影片《我,机器人》中桑尼的思想丰富。导演们在电影中使用人工智能来模拟探讨有关身份认同问题,阐述超人类主义的概念。
【欢迎转载 请注明来源】